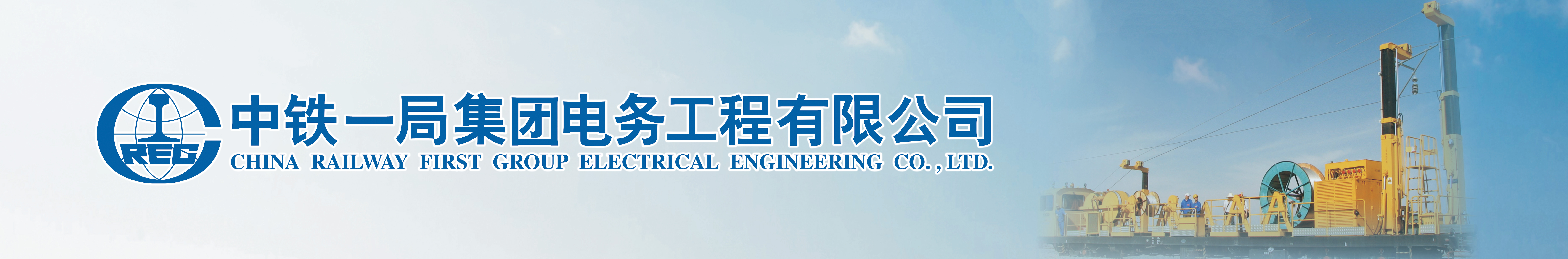赡养
刚过寒露,气温却跑赢了节气。尽管已经加了厚衣,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滩,我仍感寒意瑟瑟。
手机提示音响起,姐姐发来信息:“你给咱妈回个电话,可能找你有啥事。”母亲已是耄耋老人,拨打电话这样看似平常的举动,对她而言很是不易。我把我们子女的电话以快捷键的方式存在她的老年机上,并教她记住每个数字对应是谁。这次,她拨错了电话。
电话回过去,母亲很快便接起,我料想她应是一直在期盼中等待我的电话。
“妈,是我,打电话找我了?”
“嗯,也没啥事,现在在哪呢,都好着没?”母亲知道我的工作东奔西跑,每次总会问问我在哪个地方。
“我在新疆,都好着呢,等这阵忙过去了,我请假回去看你。”
“我在养老院啥都习惯了,她们也都不断来看我,你不用往回跑,总请假单位也不愿意(同意)你。”
母亲年迈听力很差。这次,尽管通话时戈壁滩的大风刮得呼呼作响,但在电话那头,母亲听得一字不差。
“那行,你先忙吧,不用操我的心。”母亲没有过多说什么,再次提醒我不要为她担心。
挂了电话,我意识到,自从在养老院与母亲道了别,有很久没有跟她通过电话了。我总觉自己远在他乡,力所不及的问候过于形式化,常把姐姐们,爱人和孩子常去探望母亲,当成解下感情加锁的理由。可在母亲心里,每个儿女都唯一而不可替代,越久没有听到消息,便会日日平添不安的心绪,儿行千里母担忧!
回想今年八月,在那个阴郁的午后,我开车到二姐家接上母亲,在妻儿的陪同下,一起前往养老院。
此刻,车停稳后,大家七手八脚,帮着搬下母亲的老年手推车,收拾随车的生活物品。护工从车上扶下母亲,院方在门前为母亲做了一个极简短的欢迎仪式。
母亲推着老年车,在众人簇拥下,颤颤巍巍,慢步蹒跚走进养老院门厅。一阵急风袭来,在阴云密布的天空撕开一道口子,豆大的雨点登时倾泄而下,砸在车顶砰砰作响。
那天,姐姐们帮着铺床,收拾细碎,叮嘱护工降压药和零食在床头柜里归放的具体位置。母亲用目光端详着姐姐与护工的肢体动作,虽听得不真,也能读懂。我办好了入院手续,与大家一起围坐房内,久久不愿离开,生怕使母亲萌生一丝被“遗弃”的哀怨。
此刻,倒是母亲不断催促我们:“不早了,都回吧。”
这家养老院坐落在西安老城区,与母亲住的小区仅隔一条马路,养老院曾是一家社区医院,扩大经营后增加了养老服务,所以母亲对此并不陌生,另外不用出门便可就医,对老人也十分友好。
从最初的茅草房到平房,再到旧城改造原地安置的楼房,父母在这里生活了六七十年,始终不曾离开过。短暂的人生抵不过时间的无常,2005父亲去世后,母亲仍坚持要求一个人住,小区的老邻居和一草一木,她都难以割舍。但一转眼她愈发老了,老得连上二楼回家也成了一件难事儿。
我给母亲买了一台麻将机,并邀约她的麻友前来,以使她不用下楼就能在家中娱乐。当然,我本是有私心的。一来,邻居们可以陪母亲消遣;二来,万一她有个头疼脑热,也能有个给我“通风报信”的人。之前,除非病的抗不过,她都不会给我们打电话,自己吃点药悄悄挨着,这也是最令我们做子女担心的事儿。
“你看麻将机有谁要,把它卖了吧。”我很惊讶,毕竟我看邻居们陪她在家玩得也挺开心,没过多久母亲怎会这样说。
“那老刘头不爱讲卫生,‘喀嚓’咳嗽不停。老张一会去一趟厕所,冲一下马桶,打牌还要开着灯,费水费电,我看电视就行,不打麻将了。”
母亲出生在民国,经历过饥荒与战乱,一路颠沛流离来到西安,虽然早已过上安稳的日子,但节俭的习惯已融入骨髓。我知道我无法说服她,在她的坚持下,新买的麻将机盖上盖板,很快便成了家里第二张餐桌。
想给她找个保姆,更是被母亲断然拒绝。“找个保姆,花钱找不痛快。”小区几家邻居为老人找的保姆都不如意,老人们闲聊中以讹传讹,使真相本身被严重妖魔化,所以母亲对保姆有一种天然抵触。
既然母亲日子过得仔细,那就将计就计。
“妈,现在壮壮(我儿子)上学也正花钱,这马上冬天又到了,我房子交着暖气费,你这也要烧着暖气,不如你跟我住,把这房子租出去,一进一出,一个月可省不少呢。”
“房子能租多钱?”
“我问中介了,估计能租一千七八呢。”
听完这话,母亲只考虑了一下,便说“那行。”
带母亲在我的小区熟悉新环境,她学会了独自乘坐电梯,知道了小区内的路和单元号。但家里那只厚重的防盗门锁,无论她怎样费力,都拧不开,为此我立即购买了指纹锁,解决了出入问题。
我住的小区是新建小区,居住着五湖四海为生活打拼,买房定居的大批新移民,他们年轻、忙碌,每天行色匆匆。白天的小区空空荡荡。我原来以为生活条件和居住环境都比以前好,母亲应该很满意。后来我发现,没有了老邻居,老朋友,母亲独处的时间,失去了光彩。白天当我们离家工作,家中只有“果果”(小贵宾犬)与她做伴。
有一天,我回到家,母亲开心地跟我讲起,在楼下认识了一个老婆儿(老太太),小她十几岁,山西人,能聊得来。
“很好呀,这下你有伴儿啦,天凉了,你也可以叫她来家里聊。”我说。
后来我见过这位老太太。由于方言各异,母亲听力又不好,她们交流起来很吃力,基本都是东拉西扯,你说你的,我讲我的,不时还要点个头装作听懂,其实压根对不上频道。她们约定,只要天气好,每天在楼下见面,那段时间午休过后,母亲会准时推着老年车,牵上“果果”下楼赴约,显得很有仪式感。
“那个老婆儿走啦。”
“楼下那个老太太吗?去哪了?”
“儿子在外地做生意,跟着去了,她说今年不会再回来了。”
忽一日,当母亲再提起那位老太太,眼神中流露出淡淡的忧伤与不舍。这像极了小朋友正开心玩耍,却被各自家长强行带回家时的那种不情愿,不过孩子们的娱乐方式还有很多种,这种不快很快便会淡忘,而年迈的母亲除了重回孤独,什么也做不了。
与我一起生活的日子里,母亲改掉早睡早起的习惯,经常晚上坐在沙发上,收看戏曲频道豫剧、京剧、黄梅戏还有些叫不上名的小剧种,反复重播的戏剧,直到很晚。我说:“你早点睡吧。”她说:“睡太早,早上醒得早。”
早上,母亲总是在我和爱人起床洗漱完以后,才走出她的房间。我曾悄悄推开过她的房门,看到她在床上翻来覆去睡,且轻声叹息的那种煎熬。我对她说:“早上睡不着,你就起来屋里走走,锻炼锻炼。”她说:“你俩儿上班都辛苦,早上多睡一会,我起来就影响你们休息。”
“我跟你说个事儿,你可不要多心。”
“啥事,你说。”
“小区对面那个养老院,我当时去看过,条件还可以,熟人也多,你把我送过去吧。”
我回绝了母亲的提议。我知道,是我过不了心理关,我甚至眼前已浮现送母亲去养老院时,一路之隔的邻居们在背后指指戳戳,议论子女不孝的一幕。我同时又很羞愧,母亲被“囚禁”一般的生活,除了使我心安,却不能给她的晚年带来快乐。
即便这样的生活,也很快被打破。由于工作性质的变动,我需长期驻在外地,爱人平时工作忙碌,加班成为常态,每天早出晚归。这加剧了母亲的孤独感,同时也让我们做子女的更加担心母亲独处时的安全问题。
二姐主动放弃与女儿一家的团聚生活,从南方返回西安,接母亲到家里专程照顾。可是一年来,母亲两次出现心动过缓紧急送医,加之姐夫也住院两次,二姐两头照顾,日子过得一地鸡毛。
二姐说:“没事,她能应付。”但我觉得,母亲养老的事儿必须重新考虑了。
我问母亲:“养老院,你真的愿意去吗?”
“愿意,离家近,熟人多,楼下就是医院。我去了以后,你们也都安下心了。”母亲说。
母亲入住养老院的消息,在小区不胫而走,老邻居们纷纷前来探望,一路之隔就是熟悉的小区,如果母亲想去,护工会送她过马路,待聊得尽兴后,再接她回去。我不去想以后会怎样,母亲像是重新回到阔别已久的自己的家,身边多了更多同龄人的陪伴,生活变得充实,这对于风烛残年的她来讲,未免不是最好的选择。我知道,去养老院她不是为自己,这解决了我们因赡养而面临的无奈和焦虑,母亲的通透令我感动。此刻我已不再担心旁人的议论,甚至为之庆幸。
又是一年重阳节,家家都有难念经,老吾老以及人之老,愿天下老人晚年都能有个好的归宿。